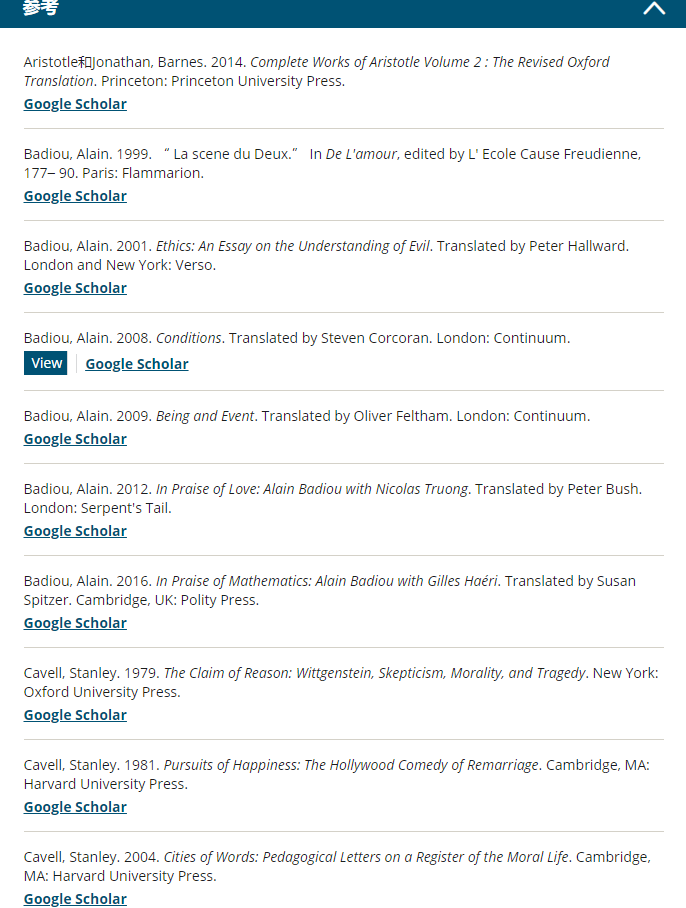文丨异文录
编辑丨异文录

摘要
本文对阿兰·巴迪乌的浪漫爱情理论进行了批判性的介绍和发展,其核心是从一个产生真理的事件的角度来理解这一现象。笔者对照更熟悉的本体论模式来讨论这个概念::作为主体的意向态度,作为内在价值的活动。
笔者认为爱情的事件概念是前者的一个更好的选择, 本文的分析集中在它与后者的互补关系,以斯坦利·卡维尔的婚姻理论为代表。进一步的论点是关于性在爱情的最终概念中的位置,通过转向罗杰·斯克鲁顿对性的内在意义的描述,来弥补笔者所认为的巴迪欧对这个主题的处理的缺点。
本文是关于阿兰·巴迪乌作品中提出的浪漫爱情理论。笔者把这个理论称为重大事件爱的概念,因为它的基础是根据一个产生真理的事件来理解爱。
巴迪欧的观点深深植根于他包罗万象、错综复杂的哲学体系中, 迄今为止,他对这一主题的观点大多是在这一体系的解释背景下讨论的,从未被认真阐述为爱情哲学主题导向领域中的一个可行立场。我在这篇文章中的目的是填补这一空白,认为巴迪欧的爱情观抓住了构成我们浪漫经验领域的思想的形而上学核心,并能够解释其必要的不变结构的阵列。
然而,为了释放这种现象学的潜力,我允许自己将巴迪欧的论文与其原始背景分离开来,将它们与其他一些关于恋爱现象的理论进行对话——最重要的是斯坦利·卡维尔和罗杰·斯克鲁顿的理论。

作为意向态度的爱:爱情观
将爱理论化的第一种也是最常见的模式是从主观意向的角度来看待它, 而它最广泛的版本——在外行人和哲学家中也是如此——是将爱认定为一种情感。举例来说,拉贾·哈尔瓦尼在一篇旨在对该主题进行最全面介绍的文章中,概述了爱情概念澄清所涉及的问题,似乎将这种认同视为理所当然:“浪漫爱情是一种类似于其他情感的情感,比如仇恨、同情、嫉妒和愤怒,还是完全是其他东西,比如欲望或态度?”
一些爱情理论希望将爱情视为一种必然的对称关系,或者将互惠作为其基本特征之一,但这些理论仍然将意向态度——尤其是欲望,作为构建其解释的主要本体论单位。举例来说,著名的罗伯特·诺齐克,强调了对这一现象至关重要的共同身份的形成,将浪漫爱情定义为不足的形成一个我们和那个特别的人。

因此,正如诺齐克所承认的,也正如这种思考爱的一般模式一样, 互惠对于爱的核心概念来说仍然是外在的,这使得单恋成为一种逻辑上不完美的爱的存在模式。
无法将主观立场的双重性作为现象的内在维度,与另一个很少讨论的理论化爱情的色情模式的缺陷有关: 爱情主要是作为一个爱人的经历来讨论的,而被爱的经历仍然是次要的 ,只要不是完全被忽略的话。最后,尽管它把主体的态度作为爱的主要媒介,性爱的概念不能公正地对待作为世界现象的爱的客观的、物质的方面。
作为活动的爱:实用主义的爱情观
亚里士多德的概念里,菲利亚通常被翻译成友谊,可以被视为爱情的实用概念的范例。众所周知,亚里士多德将人类生存的最终目标确定为幸福,理解为灵魂与美德相一致的活动,他认为,美德活动中的分享有助于更好地实践,并以其自身的权利构成一种善,是道德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幸福。从这个意义上说,菲利亚在它的最高形式中,基于美德,而不是兴趣或快乐——“是一种优秀或意味着优秀,而且是生活中最必要的”。

虽然在亚里士多德的讨论中,我们认为浪漫的爱情是两个极端中的一个,与之相关的是良性的友谊,是中庸之道。菲利亚涉及一些特征——特别是某种伙伴关系的概念——我们通常会将它与浪漫关系的最佳情况联系起来:“生活在一起,分享讨论和思想”。
此外,虽然大众通常认为亚里士多德的朋友是两个从事哲学、政治、体育和偶尔战争的男性公民,亚里士多德的评论“男人和妻子之间的友谊似乎是天生的”激励,如果不是制裁,一些现代人试图转换幸福的概念菲利亚变成了一种爱情关系的描述。

与性解放相反,在性解放中,性是以其自身的术语来描述的,福柯将爱定位为一种框架,在这种框架中,性为“创造性生活”提供了基础——一种可能性, 希望不会禁止任何性取向的爱好者,并且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与爱的最终概念完全一致。
爱的事件概念
从根本上说,爱情的事件概念不是我们感觉到或做的事情,而是发生的事情——体现在我们的情绪中,要求我们采取行动,从而使我们成为我们自己。巴迪欧爱情哲学的核心实际上是一件非常特殊的事情:事件在强烈的本体论意义上。这一概念源于马丁·海德格尔。不同于我们,他们认为发生在一些预先存在的现实坐标中的常规事件,这种意义上的事件是这些坐标本身的出现。

就先前的事态而言是不可思议的,这一事件开创了一个新的可理解性框架——海德格尔和巴迪欧都称之为“真理”——通过与支持它的秩序决裂,而不是作为那个秩序的结果。海德格尔将这种自发的开端称为世界开放——巴迪欧也采用了这一措辞——从而强调了它为相关人员采购的新的总体性,这些人因此构成了一个历史群体。

现在让我们更仔细地看看恋爱现象的内部构成,阐明事件概念所假定的本质上的时间或事实上的叙事结构的必要时刻。爱情始于遭遇,对巴迪欧来说,这是所描述的意义上的术语“事件”所适用的特定时刻:正是“事件地点”启动了“求爱程序”。
现在,这里的发现似乎同样令人着迷和琐碎:两个个体的相遇在概念上被暗示为我们在爱情方面想到的任何情况的叙事出发点。然而,巴蒂欧的主张远没有那么琐碎,而且更有见地的是,尽管在相遇中两人相遇,但只有在这种相遇中,两人才成为他们自己。
这种相遇是“两者的来临”,因为它创造了差异,这种差异将为恋爱事件的主体定义可理解性的基本条件——世界。正是由于这种激进的生产本体论,正如巴迪欧所设想的,相遇的时刻“并不进入事物的直接秩序中”;一个世界开放“不能根据世界规律来预测或计算”。
相遇的那一刻——迷恋的狂喜和一见钟情的神话——是文学和电影中最著名的时刻之一,也是情侣们在个人叙述中不断重复的时刻。
然而,巴迪欧的爱情观的另一个核心原则是,尽管相遇至关重要,但它只是爱情的起点,而不是爱情最终实现的地方。事实上,这种说法是,相遇成为一种追溯性的爱的事件且在一定持续时间内。巴迪欧认为,“爱情不能被简化为第一次相遇,因为它是一种建构”。

进一步审视忠诚和真理程序的概念,将使我们能够看到爱情的最终概念相对于性和性的概念而言是怎样的。
对巴迪欧来说,爱情现象中涉及的基本主观结构是对事件的忠诚。当然,这并不是否认过多的强烈的主观体验,这些体验把另一个人作为它们的意向对象,并且可以说构成了爱的最直接的现象“界面”。然而,根据事件的概念,所有这些都建立在多情主体与产生真理的事件的更原始的关系中,作为存在意义的非主观来源。

性在爱情的最终概念中的地位
澄清爱和性之间的关系是任何浪漫爱情理论最困难的挑战之一,对我们来说,这是对性的必要解释,这里指的是性活动和其构成潜力是作为恋爱真相程序的必要维度和时刻。
在巴迪欧早期的爱情观中,性出现在性别差异的主要概念之下, 正如巴迪欧所说,定义了恋爱事件中的差异分离。事实上,一些解释者认为这是他的理论的最基本的方面之一,但我不可否认地发现这是最没有现象说服力的。

将性纳入爱的终极概念的另一种方式——比如将它从物质表达方式提升到利害攸关的问题——应该从浪漫爱情的概念中获得线索,这些概念从体现的存在问题方面来解释它。因此,举例来说,对于卡维尔来说,婚姻实践的形而上学意义源于他对爱情的理解,即把一个人“承认他人存在和揭示自己与他人相关的存在”的一般能力押在一个独特的人身上,其必要的性成分是占理解性为“领域的有限性,其接受和反复克服的幻想是制定出来”。
笔者认为: 可以说,性作为一个领域的先验意义,在这个领域中,物质性在我们作为自由的存在中的构成性作用得到了承认,满足了与性爱事件的构成相关的追溯性因果关系。
正如Scruton所说,性爱是“对强加的命运,欲望的命运的回应”,它“立刻成为爱,但只是因为它被这样解释”。用性接触代替性欲,并把“立刻”与巴迪欧所理解的宣告时刻联系起来,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结构上,这种解释符合巴迪欧的概念,即事件在其启动的真相程序过程中追溯性地获得其事件状态。